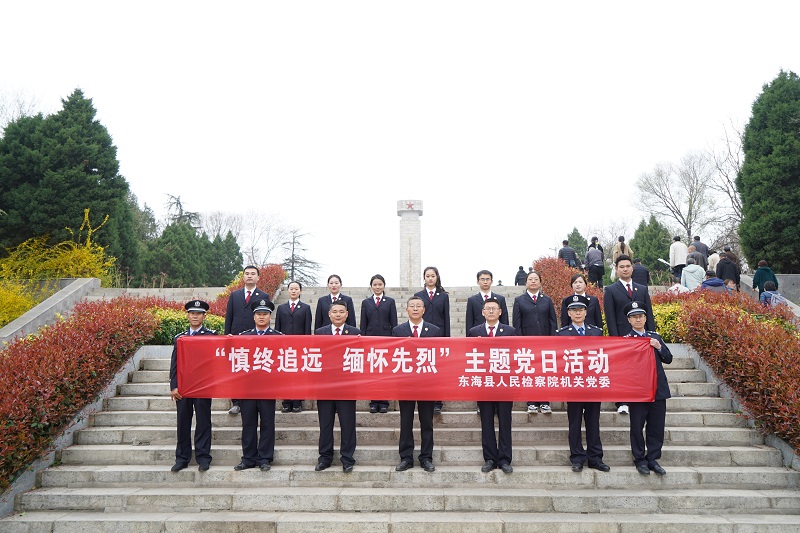常见的风景

水窖

沙地枯草

丰收了
我6岁那年,随父母从遥远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饶河县来到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第二师管辖的一个农场,甘肃省庆阳地区环县大吧咀。这儿四周全是裸露的高山,一色的锈黄。恰逢冬天,冷得出奇,僵硬的树杆,干枯的毛草在野风中摇摆、颤抖、截枝……
我被眼前景象吓哭了,嚷着要回去。母亲把我搂在怀里,用责备的目光瞅着父亲说,你看看,来到这个鬼地方,不是坑了孩子吗?父亲满不在乎:这地方有山有川、有草有羊,往后不愁有肉吃。一番话着实让我绝望。
1.
我们住在农场场部的两间平房里。农场没有电,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做饭没有煤,烧蒿草、麦秆、玉米秆、高梁秆,也买农民担来的一捆捆山柴。
场部有一群娃娃,没有学上,整日里用铁锨挖屎壳郎,用手捧着,洗干净后藏在口袋里,生怕被父母发现,挨一顿打。有时钻进放羊人避雨的土窑洞里,扒开柔土,寻找一种叫“花媳妇”的虫子,逮住了就装入早已准备好的小玻璃瓶内,听虫鸣叫。大吧咀交通不便,大人们出门不是骑马,就是骑驴,坐牛车,也有很少几辆自行车,老式的,能带三四个人。我们这帮小孩子虽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哪里也去不了,只能满地里胡跑乱撒。
大吧咀近靠宁夏,有少量的半干旱草地,牧业比较兴旺,属羊最多。冬季里羊儿们都膘肥体壮,正是宰杀的好季节。农场暂时还没有养羊,就从农村买了二十几只,宰杀后每户一只。羊皮给了农民,头、蹄、下水全扔了,不像现在,羊头、羊蹄、下水都上了席面,均能做成美味的大餐。羊肉虽嫩,但有膻气,我吃不惯,不停地唠叨太难吃了,以后再也不吃了。
看场部大门的大爷是本地的农民,从家里捉来一只大公鸡,红色的鸡毛,着实让我们喜爱。大爷把鸡递送给我的母亲说,把它杀了,给孩子们吃。我心肠软,又喜爱大公鸡,嚷着不准杀鸡。大爷笑着走了,母亲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起床后发现大公鸡不见了,院子里乱飞着红色的鸡毛。我号啕大哭,两个弟弟也跟着哭,在地上打滚。晚上,屋里飘着鸡肉的香味。母亲擀了长面,碗里都有几块鸡肉,我们兄弟三人个个吃得很香,再也不喊让母亲赔大公鸡了。
过了冬季,场部迎来了一百多名知识青年,成为兵团战士,有男有女,有长得好看的,也有长得难看的。小孩子们都喜欢好看的,难看的我们不予理睬。长得好看的给我们水果糖、花生、瓜子,我们双手接住,口袋里装得满满的;长得难看的给我们水果糖、花生、瓜子,我们风似地一跑而散,让他们很丢面子。好看的就舒心地大笑,有的捧腹大笑,有的笑出了眼泪,有几个好看的女知青说我们真逗,好玩。
知青们无忧无虑,整天的唱歌,吹口琴,拉二胡、弹琵琶,跳《北京的金山上》的舞蹈。他们能歌善舞,给这荒僻的农场带来了勃勃生机。
好景不长,知青们大多数被分配到各连队去了,只有十几个留在场部。离别时,知青们恋恋不舍,还有抱在一起痛哭的。有好看的对我说,你去跟你爸说,不要把我们分开。我的父亲是场长,我去跟爸爸说了,爸爸训斥我不要管大人的事。我就大哭,抱住爸爸的腿,求他不要分开他们,但怎么哭都无济于事。
大人们都很忙,场部只剩下一群孩子,实在无趣,就缠着留守场部的男知青给我们做弹弓。弹弓是用粗铁丝折的,然后找来红色的张力很大的橡胶皮拴在弹弓上,再拴上熟牛皮,弹弓就做成了。我们拿着弹弓打树上的鸟,但总跑靶,个个气得不行。男知青替我们打过一次,打下来好几只麻雀,糊上泥,放进火里烤,不一会儿就嗅到了肉香。剥了泥土,整只鸟不沾一点毛。一群孩子大呼小叫着抢鸟肉吃。
有一天傍晚,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父亲风尘仆仆地回来,高兴地抱起我说,儿子,你明天就可以上学了。我喜出望外,从父亲的身上蹭下来,跑到院子里大喊,上学了,我明天就要上学了。顷刻间,从场部的各个角落里跑出一群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围住我问这问那。当晚,母亲没有睡觉,连夜为我纳了一双布鞋,第二天早上,又在场部小商店给我买了书包、铅笔、本子。
2.
我们有三位老师,全是女的,个个长得好看,脸白白柔柔,像落在地上的雪。她们十七八岁,身材窈窕,留着长辫。我觉得她们像仙女。有一位女老师忽闪着眼睛看着我,嘴角挂着微笑。我瞥了她一眼,赶快又把头低下,不敢再看她的眼睛,臊得满脸通红。
开学的第一天我被选为班长。那种神气劲儿就别提了,比喝了蜜还甜。上课了,留着长辫子的女老师走进教室,自我介绍叫王秀春,以后你们叫我王老师。她的话音刚落,我便大喊一声,起立!同学们刷地一声站了起来。王老师先是一愣,尔后友好地向我笑笑。
王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七个大字,我们就跟着老师一字一字朗读。
我家离学校很近,只隔两排房,通常我听到上课铃响后才从家中出来,跑向教室。有一天早上我睡过了头,太阳已从窗户照到我睡的炕上。我不敢起了,因为我尿了床,湿了一大片。父亲开会去了,母亲天不亮就出去了,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三人。第一节下课的铃声响了,王老师推开我家的门,气呼呼地一把揭开我的被子,见我赤条条一丝不挂,脸刷的红了,背过身去说,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还睡呢!我害臊,放声大哭。王老师坐在炕沿上:哭啥。我说,我尿床了。王老师乐了:这有什么关系?小孩子都尿床的。我说,我都6岁了。王老师说,快起来,我给你穿衣服。我穿好衣服,王老师把我尿湿的褥子、被子晒到了院子里……
干裂的风不停地吹着,夹杂着狼群的叫声,荒原布满了恐惧。一天早上刚睁开眼,几个男知青风急火燎地敲我家门。父亲正在刮胡子,打开门问出了什么事?来人答,狼跳进羊圈里,咬死了二十几只羊。父亲匆忙地和几个知青出门去了,我赶紧起床,跑到羊圈想看个究竟。可怜的羊倒在血泊中,睁着恐怖的眼睛,让人害怕。
父亲说,把羊分了吧,给大伙改善一下伙食。他手指着圈门说,圈门要加固,晚上派民兵巡逻,组织打狼队。那时候哪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有一个男知青一晚上就打死了两只狼,即刻成为英雄。人们给他披上了大红花,上报上级记功奖励。
大吧咀这个地方吃水困难,到了冬天就吃雪水。落在地上的雪很干净,人们用盆、桶、锅盛满了雪。父母顾不上干这些,我带着两个弟弟在地上铲雪,其他的孩子也帮我们。老师鼓励我们帮场部大灶铲雪,我们都积极响应。我们的脸和手冻得通红,棉鞋湿透了,手和脚冻肿了,晚上特别痒,痒得我难以入睡。第二天早上起来,脚肿得穿不上鞋,只好拖踏着鞋。王老师见了心疼得不行:都怪老师粗心,让你干活成了这样子。我一仰头说没事,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那时候崇拜的英雄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红灯记》中的小铁梅。我们所处的时代英雄无处不在,英雄无处不有。
冬天的日子是漫长的。我们早早到了教室,架好了火盆,等着老师来上课。直等到灰冷的太阳悬挂在中天,也不见老师的影子。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王老师来了,脸上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甜甜的笑,双眸沉甸甸的。我们预感到了什么不幸,大气不敢出。她说,今天不上课了,大家都回去……什么!不上课了?同学们吃惊,愣愣地望着她。她说,课是不上了,但你们不能荒废自己。她打开语文课本,布置作业:一至二十八课的课文每课抄一遍,每个生字写十个。又打开算术课本:从一加到一百……说着说着她哭了,掏出手帕擦眼泪。
原来,场部来了工作组,停止生产搞整顿,学校老师也不例外。王老师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爸爸病了,病得很重。工作组在场部待了一个多月,走了。学校又要开学了,但放寒假的时间到了,而老师们纷纷回家探亲。王老师回兰州了,我站在场部的大门口,目送着她从我的眼前消失……
3.
到了五月,闷热侵袭着。山上的树,地上的草被太阳炙烧得抬不起头来。牛羊太多,很快就啃完了地上的草,光秃秃露出了地皮。
干旱来临了。天不下雨,涝坝的水也逐渐干了,人畜吃水都成了困难。旱原上打不出水,就是打出水也是苦水。农场的人们开始挖水窖,学生们也不闲着,排练节目,到工地给叔叔阿姨唱歌。那时看过电影《红旗渠》,农场的知青们学着《红旗渠》的主人公那样开展劳动竞赛,干得热火朝天,再苦再累也不吭不哈。我们被他们的精神感动,拿起铁锨铲土,用筐抬土。手磨出了血泡,肩膀压得红肿,可我们硬是咬牙坚持住。
水窖从地里挖下去,直径两米,深度十米左右,然后用红胶泥上下抹了,遇水不渗漏,不脱落。水窖挖了十几眼,就等着天下雨。但天公不作美,不洒一点甘露,明晃晃的太阳直射着,地皮发烫,草木枯萎。
人们拉水,跑上百里地,到宁夏境内的大水坑去拉水。男知青们用架子车拉,回到场部就累得东倒西歪。水少得可怜,每家不到一桶。为了节约用水,毛巾用水浸湿,全家人轮流在脸上擦擦,算是洗了脸。洗碗水舍不得倒掉,澄清了,再一次洗碗。往常狗喝洗碗水,现在喝不上洗碗水了,狗们渴得趴在地上直喘粗气,呼哧呼哧的。
人拉水劳动强度太大,很多人都累趴下了。父亲向师部求援,师部派了两辆汽车拉水,一天两趟,解决了吃水难问题。打好的十几眼水窖也灌满了水,足够用一阵子了。但水不能乱用,有定量,每天每户一桶水,水窖有民兵扛枪守着。
终于,秋天来了。起风了,天上有了乌云,电闪雷鸣,雨下来了,有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有倾盆暴雨。清亮的雨水流进水窖里,满满当当的。水窖的水澄清了,我们一帮孩子爬在井口看井里的水,我们的脸倒映在井水里,比照镜子还亮。
可以用水洗脸了,洗脚了,男人们打一桶水站在阳光下洗,女人们则在屋里拉了帘子爽爽快快地洗一个澡。干旱的日子远逝了,清香的日子来临了。女人们的头发黑亮,脸蛋细嫩,散发着雪花膏、凡士林、棒棒油的香味。
家里养了一只狗,黑色的,白眼圈,白爪子,看上去很凶,用铁链子拴在家门口,看家护门。我背着父母给狗吃肉,吃馒头。狗懂得报恩,不时地给我摇尾巴,朝我汪汪。也养猫,金黄色的,像小老虎。猫逮着老鼠就躲在墙角美餐,人若靠近,它就发出嚎叫。猫是公猫,行动神速,能逮着地上的野鸽,树上的鸟。还养了一只羊,羊是场部的——立秋后,每家都认领了一只羊。还配发了黄豆、玉米、麸子,防备羊在立秋后减膘。侍候狗、猫、羊的活基本上不用大人,都是我们兄弟三人包办了。动物们个个吃得膘肥体壮,皮毛油亮,人见人爱。
秋天眨眼就过去了,冬天又来临了。南飞的大雁鸣叫着,一会儿排成人字型,一会儿排成一字型。树叶落了,鸟落在枝杆上抖瑟着,大声吵闹,像在咒骂季节的寒冷。猫狗羊都换上了新毛,威武神气,我们也穿上了厚厚的棉装。
下雪了,大人们用扫帚、铁锨把雪堆起来,倒入水窖里。孩子们也不示弱,帮着大人堆雪。孩子们都知道用水的艰难,格外珍惜每一滴水。每年冬季,只要下雪,不用大人吭一声,我们都自觉地扫雪、堆雪、铲雪。
4.
我上了二年级。这年冬天我家热闹了起来,家在陕北老家的四姨、堂姐、表姐来到农场,成了这里的知青。听父亲说,老家比这里更苦,就把她们带出来。她们的陕北话,我听不懂。表姐手很巧,剪得一手好窗花,无论是蝴蝶、牡丹、十二生肖,还是充满农村气息的劳动场面,都剪得栩栩如生,博得众人的夸赞。堂姐善讲民间故事,晚上不睡觉,一直听到无法坚持下去才作罢迷迷瞪瞪睡了过去。我第一次从堂姐嘴里听到了兰花花,听到了三十里铺……四姨善做针线活,纳出的鞋底厚实好看,一看就耐穿。
冬天还没有结束,父亲说农场要解散,与泾川县的红卫农场合并。不久,场部开始搬迁,连队的知青们已有一部分开拔去了红卫农场。那些日子里我总是焦躁不安,不知什么时候离开这里。有一天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大人们很快就将家具搬上了卡车。我想到了狗,狗怎么办?猫可以带走,羊交到场部已经被集体宰杀了。我必须带上狗,可父亲不同意,母亲硬是把狗给了当地的农民。我又气又急,哭地昏天黑地,弟弟也跟着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汽车驶出了场部,加速朝宁夏方向驰去。我坐在车厢里,分明看见我家的大黑狗疯狂地追赶着汽车。汽车太快了,甩远了狗。我的眼睛模糊了,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一幕,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却总让我从梦中惊醒。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检察院)